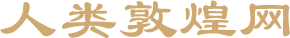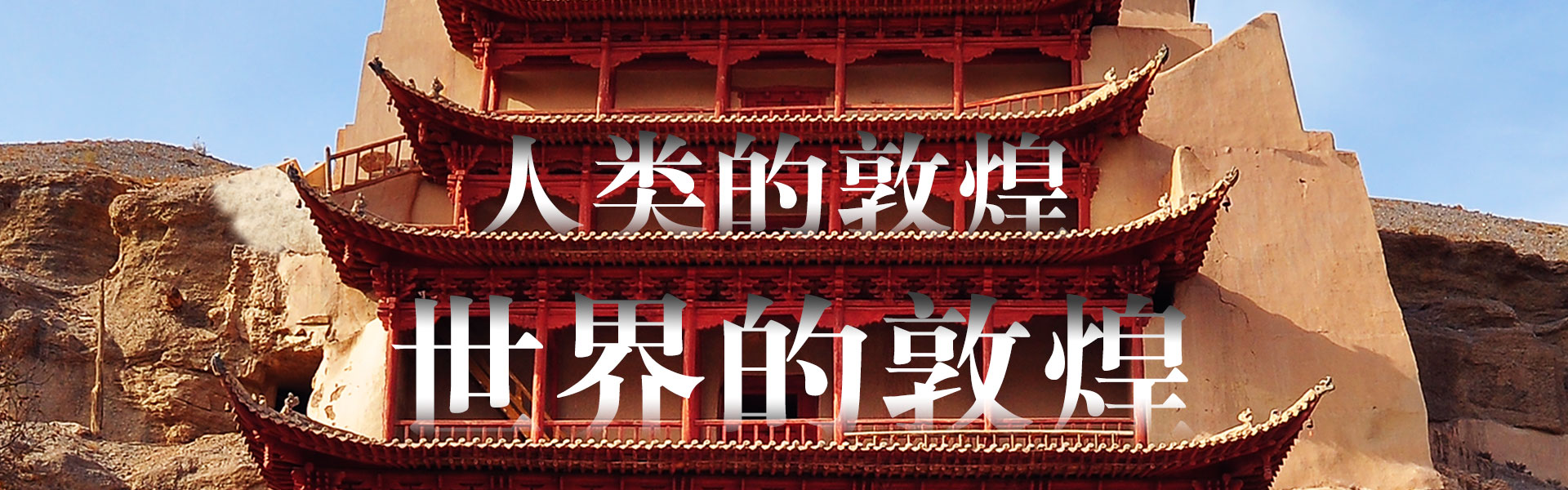敦煌样式的文化主体

只要我们的目光一触到敦煌的画面,心灵即刻被它这种极其强烈的独特的审美气息所感染。从艺术上说,敦煌壁画是东方中国乃至人类世界一个独有的样式,这便是敦煌样式。如果我们确定这一个概念,我们就会更清晰地看到它特有的美,更自觉地挖掘其无以替代的价值,并甘愿被征服地走入这种惟敦煌才富有的艺术世界中去。 敦煌样式的文化主体 在海上丝路开通之前,中国面向外部世界的前沿在西部,其中一扇最宽阔的大门便是敦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自神州腹地中原喷涌而出,经由河西走廊这条笔直的千里通道,穿过敦煌,向西而去,光芒四射地传布世界。同时,源自西方的几大文明,包括埃及文化、希腊文化、西亚文化,以及毗邻我国的印度文化,亦在同一条路线上源源不绝地逆向地输入进来。东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便在这里的大漠荒滩上撞出一个光华灿烂的敦煌。 然而,敦煌却不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物与化合物,也不是多种文化相互作用后自然而美丽的呈现。它有一个主体,就是中华文化。我们可以从莫高窟壁画史清晰地看到外来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和希腊化的佛教艺术渐次中国化的奇妙过程。但是中华文化只是一个大主体。它中间还有一个具体的强有力的地域性的文化主体,便是敦煌一带的历史主人——北方少数民族。 敦煌内外,自先秦的戎、羌、氐、大夏,到两汉时期的塞人、胝人、匈奴人、乌孙人,都曾轮流地称霸于此。在莫高窟的开凿期,柔然鲜卑和铁勒突厥就是在这里当家的主人。而整个莫高窟的历史中,吐蕃、党项、回鹘、蒙古,都曾做过敦煌的统治者。中国的古城很少有敦煌这样的多民族都唱过主角的斑斓的经历。这样,无论是鲜卑、吐蕃、党项,还是回鹘与蒙古,都曾给敦煌带来一片崭新的风景,注入新的活力以及独具的文化内涵。习惯于绕行礼佛的吐蕃人,不仅带来一种在佛床后开凿通道的新型窟式,带来《瑞象图》、带来了日月神、如意轮观音和十一面观音,更带入藏传的佛教文化;党项人不单给敦煌增添神秘的西夏文字、龙凤藻井和绿壁画,而是注入了一种带着女真族和契丹族血型的西夏文化;在敦煌听命于蒙古人的时代,窟顶上布满的庄重肃穆的曼陀罗只是一种异族风情的表象,关键是这一时期,忽必烈为莫高窟进一步引进了源自印度、并被藏族发扬光大的密宗文化。相异的历史形成他们各自的风习,相同艰辛的生活却迫使他们必备同样的气质,那就是:勇猛、进取、炽烈、浪漫、豪放与自由自在。 就是这种北方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特征,形成了敦煌样式的文化主体。 从莫高窟历史的初期看,域外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总是交替出现。我们能看到两条脉络:一是中华文化主体的渐渐确立;一是西北民族的主体精神渐渐形成。若说中华文化,即是世俗化、情感化、审美的对称性,雍容大度的气象,以及线描;若说西北民族的精神,则是浪漫的想象、炽烈的色彩、雄强的气质,辽阔的空间,还有动感。 敦煌样式的成熟与形成是在莫高窟的鼎盛期——也就是从初唐到盛唐。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文化的主体牢牢确立,西北民族精神气质从中成了敦煌的主调。 这首先应归功于大唐盛世。当大唐把它的权力范围一直扩展到遥远的中亚,客观上敦煌就移向了大唐的文化中心。唐代是中原的汉文化进入莫高窟的高潮,从儒家的入世观念到艺术审美方式,全方位地统治并改造了莫高窟的佛陀世界。 只有自己的文化处于强势,才能改造乃至同化外来文化。对于外来的佛教来说,中国化就是文化上的同化。所以佛教的中国化和佛教艺术的中国化,都是在大唐完成的。这个中国化的结果便是敦煌样式的形成。应该说,在强盛的大唐文化熔化了莫高窟,并且进行再造的同时,西北民族把自己的精神溶液兑了进去。敦煌壁画有一种特有的东西——那种独一无二的敦煌样式与敦煌精神,还有敦煌的冲击力和魅力。 我们若用西北民族的精神语言去破译敦煌,一切便豁然开朗。 敦煌艺术的冲击力,首先来自那些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西北人不竭的激情。这激情在洞窟内就化为炽烈的色彩和飞动的线条,以及四壁和穹顶充满动感的形象。敦煌壁画比起山西永乐宫、河北毗卢寺、北京法海寺、蓟县独乐寺那些中原壁画,后者和谐雅丽,雍容沉静;而前者浓烈夺目,跃动飞腾,神佛也都富于表情,个个神采飞扬,不像中原壁画中的那些面孔,大多含蓄与矜持。至于在敦煌的壁画上处处可见的飞天,则离不开西北人对他们头顶上那个无限高远的天空的想象。那里的天宇,比起中原内地,辽阔又空旷,浩无际涯,匪夷所思;在这中间,再加上他们自由个性的舒展,佛教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便被他们发挥得美妙神奇,变化万端。他们还把这神佛飞翔的天空搬到洞窟里来,铺满窟顶;世界任何石窟的穹顶也没有敦煌这样灿烂华美,充满了想象。西北人如此痴迷于这窟顶的创造,是否来自他们所居住的帐篷里的精神活动?反正那些源自印度犍陀罗窟顶的藻井,早已成了西北民族各自心灵的图案了。 习惯于迁徙的西北民族,眼里和心中的天下都是恢宏又浩大。为此,在华夏的绘画史上,他们比中原画家更早地善于构造盛大的场面。兴起于隋代和初唐的《阿弥陀净土变》《观无量寿经变》和《西方净土变》,展现的都是佛陀世界博大又灿烂的全貌。我们暂且不去为画工们的构图与绘画的杰出能力而惊叹。在此,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恰恰表现了在艰辛又寂寥的环境中生存着的西北民族的精神之丰富和瑰丽。 现在应当确认,敦煌艺术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个派生的和从属的部分,而是其中一个独立的艺术样式与文化样式。对于丝路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整体的中华文化是敦煌石窟的文化主体;对于中华文化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之间的多元交流,西北民族是敦煌石窟的主体。只有我们确认这个主体及其独具的样式,我们才是真正读懂了艺术的敦煌。 元代的敦煌留下一块古碑,它刻于1384年(元至正八年)。名为“六字真言碑”。所谓六字真言碑即碑上所刻“唵、嘛、呢、叭、咪、哞”六字,分别为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6种文字。这6种文字在当时都是通用的。 石头无语,文字含情。它无声却有形地再现了敦煌当时生动的文化景观,那就是西北民族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与辉煌。 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更自豪地说敦煌艺术天下无双。